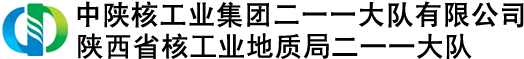年輕時,張富清備嘗艱辛。十五六歲,他到地主家做長工,后來家中唯一壯勞力二哥被國民黨抓壯丁,為了全家維持生計,他用自己將二哥換了出來。他因身體瘦弱,被指派做打掃、洗衣、做飯、喂馬等雜役,飽受欺凌,稍有不慎就遭到抽打,苦不堪言。
國民黨部隊被剿滅后,在領3塊大洋回家和參加革命隊伍之間,他選擇了后者,成為西北野戰軍的一員。自此,瘦弱的張富清爆發出驚人的能量,在壺梯山、東馬村、永豐城等戰斗中他擔當為大部隊清障開路的突擊隊員,先后炸掉敵人四個碉堡,立下赫赫戰功。
這樣一位戰斗英雄,在退役轉業后卻將過去的功績深埋心底。漫長的歲月里,除了向組織如實填報個人情況外,他從未說起過這些戰功。英雄褪去光環,回歸平凡,有苦自己咽,有難自己扛,再苦再難,他也絕不躺在功勞簿上。
若非國家開展的退役軍人信息登記發現老人的事跡,這一切或許將永遠塵封,不為外界所知曉。英雄無言,是何等崇高的境界;英雄無名,該是多么大的遺憾。去年底,他的子女們終于知道,原來父親是一位戰斗英雄。此時,他的大兒子張建國已經退休,這是多么漫長的歲月!
當我們跟隨張富清的小兒子張健全來到老人居住了30多年的家中時,昏暗的燈光、斑駁的墻壁、褪色的家具……都在無聲地講述著老人的人生故事。
在老人家中靜默地逗留尋覓,我們看到陽臺上一排像戰士一樣整裝待發的綠植,看到寫字臺上做了很多記號的書和字跡黝黑而略顯凌亂的筆記,看到角落里用了幾十年的舊搪瓷缸。
臥室里一個帶輪子的像鞋架一樣的架子,就是老人左腿截肢后行走的支撐。2012年,老人左腿感染危及生命被迫截肢,當時他已是88歲高齡。我們無法想象,耄耋之年遭受這樣沉重的打擊,老人該有多么強大的內心才能逼迫自己重新站起來。張富清的老伴兒孫玉蘭說,他多次在扶著墻練習站立時跌倒,殘肢擦在墻上和地上留下一條條血痕。
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來鳳縣是湖北省最偏遠的一個縣。1955年,退役轉業時,組織告訴已升為連職干部的張富清,恩施地區條件艱苦,急需干部支援。山水迢迢,他深知這一去只怕再也回不了大城市。雖然心里惦記著部隊,又想離家近些,他還是服從組織安排,帶著愛人來到了恩施。到恩施后,他再次響應組織號召,奔赴來鳳縣。從此,兩人扎根異鄉山區,一過便是一生。
從糧食局到三胡區、卯洞公社再到外貿局、建設銀行,在每一個崗位上,張富清都兢兢業業,甘當螺絲釘。
這是怎樣的一個英雄!當副區長,他讓自己的愛人下了崗;當革委會副主任,他把自己的大兒子下放到林場。
他從不為自己和家人謀取私利,子女沒有一個在他曾經工作過的單位上班。
他艱苦樸素,對生活毫無所求。房子,左鄰右舍都裝修一新,他家還是30年前的老樣子。衣服,袖口都爛了,他還在穿,兒子買的新衣服被他疊得整整齊齊放在箱子里。做眼部手術可以全額報銷他卻選擇最便宜的晶體。
他說:“沒法再在工作崗位上為國家做貢獻了,能為國家節約一點是一點。”
他就是這樣一個人,心里時時刻刻裝著組織,裝著國家,卻幾乎沒有他自己。
一個寧靜的下午,我們開始了和老人面對面的交流。對話在一種肅穆的氛圍中開始——
“你打仗時為什么這么勇敢,不怕死嗎?”
“作為一名共產黨員、革命軍人,我入黨時宣誓,為黨、為人民,我可以犧牲一切。我一直按我入黨宣誓的去做,對共產黨有一個堅強的信念……所以滿腦殼都是要消滅敵人,要完成任務,沒有任何其他的想法,所以也就不怕死了……”
“88歲截肢后,當別人以為你站不起來的時候,你為什么又站起來了?”
“不能工作了,我不能給國家增加任何麻煩,也不能給家里增添很大的包袱,我要他們好好工作,為黨多做點事情……”
“64年來,你立功的事情,你不對單位講,甚至也不對家人講,孩子們也是剛剛知道,這是為什么?”
“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戰的戰士,有幾多(好多)都不在了,比起他們來,我有什么資格拿出立功證件去擺自己啊?!我有什么功勞啊?!比起他們我有什么功勞啊……”
講到這里,老人哽咽難言,淚水溢滿了眼眶。他的老伴兒掏出紙巾給他擦拭眼角的淚水。他又想起了那些死去的戰友啊!此時,記者也忍不住流淚。